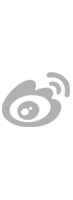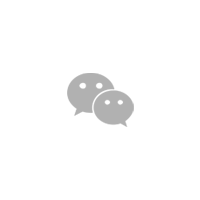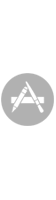中古陶春拍|對坐說法 以心印心——明代西藏西部上師對坐唐卡賞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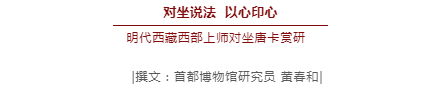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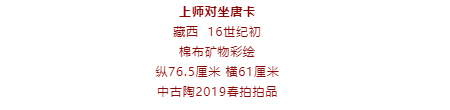
西藏西部是藏傳佛教傳播的一方寶地,從10世紀末古格王朝建立到17世紀上半葉古格王朝滅亡,佛教在這塊土地上持續發展了六百余年,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藏西部佛教文化,唐卡藝術就是其重要而突出的體現。藏西唐卡藝術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相當于10-13世紀初的后弘初期;中期,相當于13-14世紀;晚期,相當于15-17世紀初。雖然每個時期的唐卡藝術由于受到不同的佛教流派和藝術風格的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時代風貌,但藏西本土那種樸拙厚重的表現手法、淳樸自然的審美情趣,始終頑強而牢固地存續于藏西唐卡藝術之中,呈現出幽美、邈遠、神奇、迷人的藝術氣韻和風采,展現出不同于其他藏區獨特的藝術風貌。這幅上師對坐唐卡就是一幅西藏西部晚期風格的典型代表。

這幅唐卡表現的主尊為對坐的兩位上師。二上師呈四分之三姿勢側身對坐,表現二上師(多為師徒)之間的教法傳承關系。根據西藏13至17世紀流行于達隆寺和俄爾寺的上師對坐唐卡的主次排列來看,右邊一位地位要高,屬師父輩分,左邊一位地位稍低,為師父的弟子(也有隔代相傳的現象和例子)。二上師是全幅唐卡表現的重心,它們占據了畫面近乎三分之二的面積,因此繪畫者投入了最大的心智和最高的技藝進行表現。畫面上無論人物造型、衣紋線條,還是色彩、花紋、背光及臺座的描繪,一筆一畫,勾勒暈染,皆一絲不茍,造型嚴謹而不失生動,裝飾華麗而不失莊嚴,同周圍的其他人物和景物相比,可以明顯看出其高妙和優勢之所在,因此可以說二上師的表現是全幅唐卡最為精彩的部分。

上師身著僧坎、袈裟和僧裙,下身又圍著寬大的僧氅,衣服流暢,色彩和諧雅致,衣服上描繪各種花紋圖案,生動表現了上師尊貴的宗教地位。面部刻畫生動,面容柔和,氣質高雅,法相莊嚴,神態寧靜,具足藏地高僧悲智雙圓的大德儀范。而其雙目的表現尤其值得注意,都是目不轉睛的直視前方,時間仿佛停駐于他們的目光之中,上師以心印心之教法授受仿佛就在這一瞬之間。

二上師皆右手結說法印,左手分別持經書和法輪,其中左邊上師額間還戴一副黑色眼罩,據說是用于禪定或宗教儀式時遮蔽眼睛。另外,他們的周圍還各有華麗的頭光和身光裝飾,身下有寬大的蓮花座和須彌座相承托,其外繞以祥云,這些極盡莊嚴的裝身具又進一步凸顯了二上師如同佛陀一般的尊貴地位。唯一遺憾的是,盡管二上師的形象特征鮮明而具個性特點,但我們一時很難判明其各自身份。

二上師周圍環繞的尊像以傳承上師為主,分布于主尊上下左右各個方位,共33尊。其中左右分布的上師呈嚴謹的對稱之式,明顯承襲了西藏早期唐卡棋格式構圖形式。這些上師有的戴班智達帽,應為印度或西藏早期的傳承上師,而大多數為方袍圓頂的西藏上師。他們皆呈坐姿,雙手結說法印,有仰蓮臺、頭光和舉身光作為莊嚴,姿勢與裝飾整齊劃一,極大地增添了畫面的整體感和莊嚴感。

在上方正中,有三身圖像特別值得注意,自上而下依次為釋迦牟尼佛、喜金剛和薩迦派上師,標顯了唐卡內容與薩迦派的密切關系。其中,釋迦牟尼佛居于最上方,意在表示薩迦教法源于佛祖,佛祖實乃一切佛法、一切教派的共同源頭。居中的喜金剛屬于藏密無上瑜伽部修法,在無上瑜伽部父續和母續的修法中屬于母續,是薩迦派主修的本尊。喜金剛以朱砂勾勒,全身施以金彩,身后配以巨大的背光,極顯莊嚴神圣,亦在重點突出其無上瑜珈修法中的至尊地位。

唐卡下面一排圖像也很重要,包括供養人和護法神兩個組合。供養人位于左邊,為三男三女,三男在前,三女在后,皆恭敬地盤膝而坐。男子披發,著墨綠色帶花紋的袍服,女子辮發,著紅綠搭配也帶花紋的袍服,明顯保持了西藏早期的服飾傳統。他們身前擺有香爐,身后有堆積的寶珠,有的還手持供燈,顯示了供養人的明確身份。從頭飾、衣著和人物氣質看,他們顯然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一方的貴族。他們身后有兩棵直立的大樹,顯示了不同于圣界的自然主義人間氣息。供養人右邊是四身護法,自左至右依次為財寶天王、婆羅門大黑天、寶帳怙主和四臂吉祥天母,他們皆以金色身示現,各展威武姿勢,坐騎、手印及持物不一,顯示了各自不同的殊勝護法功德。其中右邊三像特別值得注意,是薩迦派獨崇的護法神,為薩迦派三大不共護法神。這三尊薩迦不共護法的出現,形成了與上面圖像教派上的很好呼應,它們又共同反映了這幅唐卡的表現內容與薩迦派的密切關系。

上面分析了畫面的圖像內容,下面來看它的風格和產地。看到這幅唐卡,首先明顯感覺它是一幅后藏俄爾風格的唐卡,其整體構圖、佛像造型、佛身莊嚴、背景紋飾、色彩搭配等,都體現了俄爾風格的鮮明特點。具體表現為:1、唐卡的表現主題及構圖明顯來自俄爾唐卡,主尊為二上師對坐,占據畫面較大面積,其他傳承上師分布于主尊的上下左右,嚴謹對稱。這種表現形式在現存的俄爾唐卡中可以看到許多實例,其中美國魯賓博物館收藏的一幅“道果傳承上師唐卡”在年代、主題及構圖上與此幅唐卡最為接近(參考圖1)。2、上師頭光和身光邊緣的火焰紋裝飾,如同精致的花邊,勾勒嚴謹細膩,是俄爾唐卡上常見的表現形式。3、各上師服飾的線條生動寫實、流暢優美,其上的花紋圖案繁密精致,也是俄爾風格擅長的技藝和慣常的表現形式。4、各傳承上師周身環繞的圓形身光,多見于俄爾唐卡上,尤其是俄爾晚期唐卡上。5、二主尊身下的蓮花瓣,形制美觀,色彩繽紛,也明顯來源于俄爾風格。當然,這些俄爾風格特點有的在欽孜風格唐卡上也可以看到,如主尊身下的蓮花瓣形制、佛像衣紋表現及花紋裝飾等,但這也不足為奇,因為欽孜與俄爾同屬于薩迦派,都出自薩迦派寺廟,都是為薩迦派服務的繪畫流派,它們之間必然有著藝術上的密切聯系和相互影響,俄爾唐卡吸收和借鑒欽孜風格的某些表現形式和手法實屬正常。總之,在總體面貌上可以說這幅唐卡明顯展現了西藏后藏地區的俄爾風格特點。

由上可見,從大的方向上確定這幅唐卡屬于俄爾風格是沒有問題的,但實際情況又非如此,因為這幅唐卡除了表現出鮮明的俄爾風格特點外,還表現了許多獨特的地方藝術和審美特色。對照西藏各地方繪畫的風格特點,這些地方特色將其產地明確地指向了西藏西部。其中最具西藏西部特點的表現有兩處:一處是唐卡左下角的供養人。以世俗供養人身份出現在唐卡下方,供養人頭飾和著裝保持了西藏早期先民的服飾傳統,這些都是西藏西部唐卡上特有的表現形式,有許多實例可以為之證明。在同時期的西藏中部和東部的唐卡上,供養人已很少見到世俗人物,而多以僧人替代。2018年北京湛然拍賣公司推出的一幅釋迦牟尼佛唐卡,產地和時代與此幅完全一致,其下方也有一排與此幅類似的供養人(參考圖2)。

再一處是須彌座前面的獅子。其身軀瘦長而勁健,不像我們常見的那種壯碩雄健、飽滿敦實的造型樣式,與其說是獅子,不如說更像狗。特別是它們呈飛奔之勢,頭部向后大幅度扭轉,四足奮力向前,尾巴高高翹起,造型極度夸張,也極具張力。而這正是西藏西部流行了數百年的獅子的樣式,現存的壁畫和唐卡上屢見不鮮,可以說代表了西藏西部獨特的審美情趣。

另外,畫面上多數上師形象比較質樸,護法神的造型比較粗獷,所有的勾勒及暈染不如衛藏細膩等,也都體現了西藏西部的繪畫水平和審美習俗。由此可見,這幅唐卡風格不能簡單地歸為俄爾風格,而應當服從于它的產地歸為西藏西部風格,或稱古格晚期風格,就如勉唐畫派影響了西藏東部、不丹、北京和蒙古等許多地方唐卡繪畫,我們自然不能把受其影響地方的唐卡籠統地稱為勉唐風格一樣。

那么,西藏西部繪畫為何會受到后藏俄爾風格的影響呢?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并不難解答,總的來說與薩迦派的傳播有關。這幅唐卡表現的主題內容其實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而征諸歷史可以找到更為可靠和清晰的依據。薩迦派何時傳入西藏西部目前尚無明確記載,但1277年八思巴召集的曲彌大法會有包括阿里等地的七萬余名僧人參加,這時的西藏西部應當受到了薩迦派的影響;同時可以肯定的是15世紀前薩迦派在西藏西部的影響一直比較微弱,遠遠不及止貢、竹巴、帕竹等諸教派,直到15世紀初薩迦俄爾支派創始人貢噶桑波來到古格,才改變了薩迦派在古格的影響和地位。貢噶桑波曾三次前往古格,收徒傳法,修建寺廟,使薩迦派一時大興于古格。當時古格修建的薩迦派寺廟有皮央寺、熱布杰林寺等,改宗的寺廟有科加寺、喜德林寺等,其中皮央和科加兩寺還成為俄爾派祖寺——艾旺曲德寺的分寺。至今在皮央的一座洞窟式的殿堂(編號N區32窟)內仍然保留了16世紀薩迦題材的壁畫,可為這一歷史提供有力的證據(參考圖3)。毫無疑問,這些史實為這幅唐卡的內容和風格都提供了重要依據:唐卡表現內容為薩迦派傳承上師系列,與俄爾欽的傳法活動直接相關;唐卡風格主體表現為俄爾風格特點,也正是薩迦俄爾支派在古格傳播的結果,因為俄爾畫風是附屬和服務于俄爾教派的繪畫藝術流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薩迦俄爾一派在古格的傳播歷史,還可為這幅唐卡具體內容的確定提供了重要參考,根據這一歷史,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前面的推測:二上師上方的薩迦祖師就是薩迦俄爾派創始人俄爾欽·貢噶桑波,而整幅唐卡表現的教法傳承就是薩迦俄爾派教法傳承系列。

綜上所述,對于這幅唐卡的欣賞和研究可以歸納為四點:其一,這幅唐卡主要表現薩迦俄爾支派的教法傳承體系,見證了興起于15世紀的薩迦俄爾支派在西藏西部傳播的歷史事實,反映了薩迦俄爾支派在雪域高原的廣泛影響。其二,唐卡的整體風格仿照了后藏俄爾風格傳統,而在一些技法和裝飾細節上融入了西藏西部的藝術和審美情趣,展現了明代西藏西部唐卡藝術獨特的風格面貌,反映了明代西藏西部佛教繪畫藝術與西藏中部交流融合的重要歷史信息。其三,這幅唐卡代表了西藏俄爾風格的晚期作品,也代表西藏上師對坐題材的晚期作品,無論是研究西藏繪畫藝術中的俄爾風格及其影響,還是西藏上師對坐題材唐卡流行的時間和地域,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四,明代西藏西部佛教以格魯派為主流,繪畫藝術以江孜風格為主流,這是以往學術界的普遍認識和看法。這幅唐卡表現的內容和風格都與薩迦派密切相關,反映了當時西藏西部佛教和佛教藝術流派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特點,可以促使人們重新審視15世紀后西藏西部的佛教和佛教藝術發展歷史,進而改變過去認識上的偏差。